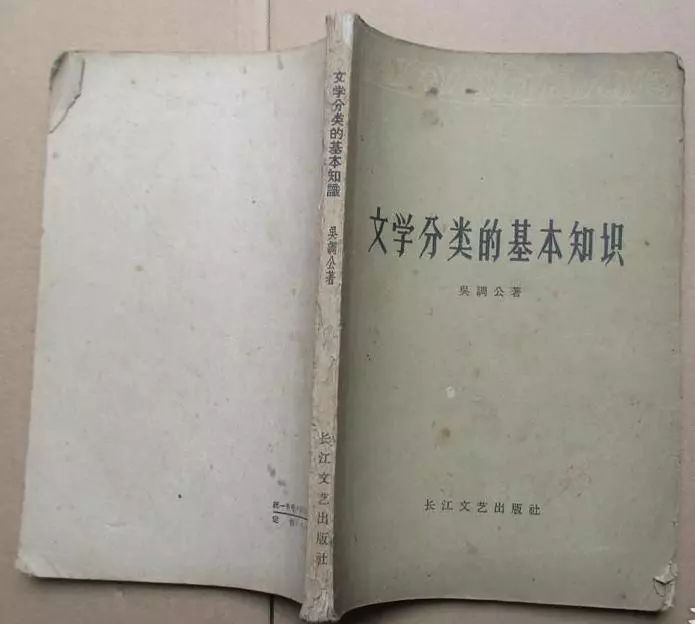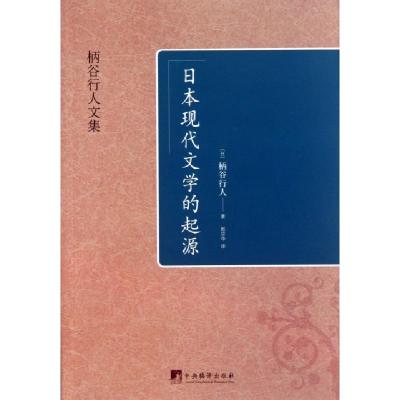谈到翻译文学,不免要牵涉到翻译问题。翻译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翻译的“保存”与“同化”。
“保存”,是指译者努力尝试进行复制——再现——原作的看得出的特征。“同化”,是指作者通过对原作的修改,使之变成一般读者熟悉的形式。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处于两者之间。
在钱钟书先生所著《七缀集》中,专门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中国第一首汉译英诗歌《人生颂》,讲述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美国郎·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的翻译掌故。
中国第一首汉译英诗歌《人生颂》
《人生颂》先由英国公使威妥玛译为中国散文,然后由中国尚书董恂据每章写成七绝一首外国人必读意大利文学名著,两种译本收在方浚师《蕉轩随录》第十二卷里。
在谈《人生颂》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认为近代中西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文本的引进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当时对外国文学与律法科技书籍翻译技巧上的区别对待。
那个年代翻译文学,是为了引诱外国人来学中文;中文小说偏爱场景,而律法、科技书籍偏重叙事技巧。
二是文学翻译叙事技巧不同。
“视角问题”是中西方文学翻译技巧区别的原因之一。英语小说通常从一个超然的视角或观点来描述一幕场景或一个人,被中译者改为从人物的角度开始描绘。
“语言关问题”是中西方文学翻译技巧区别的原因之二。。在翻译中对人名、地名、特定俚语会遭遇到特定的文化障碍。外国文学在“中渐过程”中会“变相”。
以汉译第一首英国诗歌《人生颂》为例,中介人威妥玛自身汉语水平限制造成的文学原价值减损,而后尚书董询再译时将诗歌特定背景移植入中土文化背景造成的词义牵强与谬读。

郎·费罗
三是当时学者对于外国文学认识的局限性。
当时清廷的比较文学媒介者是一些公使、参赞、随员等。他们对于出国和异国文学的态度是消极的,认为出洋凶险、是苦差使,语言的困难抑制了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好奇。
本文基于钱老谈《人生颂》一文,第一部分先尝试分析近现代中西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文学“转化和参照”的原则有哪些;第二部分剖析引起近现代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的社会文化起源;第三部分深入分析影响文本“进口”与“出口”的因素;最后第四部分谈谈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如何对待异域文本的“文化影响”。
中国最早小说译本《昕夕闲谈》
— —
近现代中西方翻译文学的“转化和参照”原则
被认为最早小说译本的是《昕夕闲谈》。最早分26期于1873到1875年发表在上海的月刊《瀛寰琐记》上,译者是蠡勺居士。
据考是曾任上海《申报》高级编辑的蒋芷湘(也有人说叫蒋其章),他写散文时用小吉罗庵主之名,写诗时用蘅梦庵主或小吉罗庵主,写通俗小说时用蠡勺居士。
《昕夕闲谈》是长篇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的前半部,其作者是英国作家利顿( )(1803-1873),原著最初出版于1841年。
《人生颂》和《昕夕闲谈》分别译于18世纪60、70年代,当时的美国、英国和中国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隔绝,面临着一大堆涉及如何处置对方文化独有的问题。
为避免理解障碍,当时的翻译以同化翻译为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化原著中的主题和人物类型,使之符合读者自己的文化。
鉴于当时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众多差异,归纳起来,学者们在译介时一般遵从以下“五大”原则:
一是选本目的。选择当时影响度较大、思想符合本民族口味的文本。

如钱钟书说明了当时朗费罗和《人生颂》的家喻户晓、传诵一时。而《夜与日》作者利顿的声望虽然在20世纪中已急剧下降,但在1870年代他仍然是最著名的英语小说家之一——和狄更斯在一个层次上。所以1879年第一部译成日文的小说,《花柳春话》,也是利顿的小说。
关于思想方面,钱钟书《人生颂》一文中说到
“阅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
董询这才重译《人生颂》。
而第一部小说《昕夕闲谈》译者在前言中提到该书将通过西方风俗扩大人们的视野,改变读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
二是形式、顺序、连续性。
18和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喜欢推迟公开人物身份,在叙事上喜欢在没有设定场景的前提下,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上,希望获得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在翻译过程中,英国小说往往被改造成典型的中国小说分章回,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注重连续性——尽可能延续同样的焦点人物叙述,因为传统的中国叙述可以在时间或焦点人物两者之间择一进行跳跃,但不可能同时两者都进行跳跃式的叙述;因此英国小说的跌宕性变得平实缓和。
三是风格、声调,语言水平。
英国小说家喜欢调侃的或反讽的委婉文体。
钓鱼被描绘作“垂钓弟兄们的最佳运动”,渔翁被称之为“邻居的沃尔顿们”。
沃尔顿(Izaak )是一部古典钓鱼著作的作者,而翻译成了中文的表达则减少成很简单明了的语言。
同时,英国人在一些场景描写时添加某些文雅的独白似的评论或叙述,都被删掉,因为中国传统的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几乎不会允许这种冗长的吐露感情的叙述方式。
四是叙事技巧。
中文小说偏爱场景,于是,外国小说中那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场景,不但在翻译中被增加,有时还加上了具体的额外的细节描写。
中文叙述倾向于将思想当作直接的引语来处理。因此,那些外国小说中冗长的讲演和叙述,通常会在中译本中被插入感叹词和问题分为对话。很自然地从概括性叙述变成了场景性叙述。
英语小说通常从一个超然的视角或观点来描述一幕场景或一个人,被中译者改为从人物的角度开始描绘。
五是接受外国文化的参照。这是文本翻译乃至文化交流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各个国家都有许多涵盖特定文化背景的词汇。
在钱钟书文章中,在翻译《人生颂》时,除了不得不把本文化中没有的因素强行删掉,在一些译本中,常采取类比的方法来翻译。
公用马车和江南航船的比较;西方葬礼上用的黑色和中国的白色相比较;西方打牌骗子的技巧和中国打牌作弊者的比较;牧师所戴的铲型帽——译者认为是学位帽——被和中国的方巾帽相比;英格兰的“爵士”称号被拿来与授给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头衔相比。
在对这些进行比较的同时,可以获得很多关于不同文化的有趣的发现。
— —
近现代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学关注的社会文化起源
在《人生颂》一文中,钱钟书说到:
“方浚师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是引诱外国人学中文,第一部汉译小说的翻译者说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西方风俗、改变对西方的态度。”
可见,两者之间对于外国文学引进的初衷已经有了不少区别和进步。
一百多年来,我国文学作品也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其他国家。我国戏剧最先介绍到欧洲的是《赵氏孤儿》,由马若瑟神父于1731年节译成法文,1735年发表。
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又以它为素材,改编成《中国孤儿》,变成一部颂扬中国道德、颂扬儒家文化、古代文明的剧作,更引起了西方人的兴味。它反过来又推动了西方“中国热”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 世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主要缘于“探求、好奇、借鉴、共通”。
一是文明“探求”。要了解到更多的该国风情、道德规范、伦理观念、文化心理等等。
这一点原因是各国普遍性存在的。如起源于民间口头创作的中国小说,尤其是与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的章回体古典小说,往往很受欧洲人的欢迎。
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认为《红楼梦》、《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
法国是最早译介中国小说的国家,1925年莫朗重译《好逑传》。1957年出版路易·阿韦诺莱译《西游记》,据统计,《红楼梦》迄今有英、德、法、意、俄、日、捷、匈、罗、希腊文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

二是对新中国的“好奇”。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上。
新中国的出现,人们急于窥察这个伟大国家的新貌,当时不能亲临考察,往往通过文学作品这条捷径。
在法国50年代初,最早传递现、当代文学信息的是《欧罗巴》文学月刊于1953年推出的中国新文学专号,载有鲁迅、艾青等现代作家的作品。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翻译出版了艾青诗选、闻一多诗选和文集、郭沫若诗选和文集、老舍文集、孙犁文集、康有为作品选等匈牙利、罗马尼亚、墨西哥、瑞士、意大利、美国都翻译了王蒙作品。

三是借鉴以寻求本国文学发展道路。
日本,一部分文学家为了抵御和摆脱西方文化日益强大的侵压,意识到以新的角度发掘和评价日本文学传统中优秀成份的必要性,同时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以寻求日本文学发展的道路。
郭沫若、茅盾、老舍、丁玲、赵树理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家,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兴趣。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也为日本译者所瞩目。
四是社会历史观点的共通。
苏联汉学家的著作别具特色,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重视作家作品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他们喜欢翻译革命家、尤其革命烈士、在创作方法上看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
鲁迅、老舍、茅盾、闻一多、艾青、曹禺、瞿秋白、郭沫若、殷夫、秋瑾等得到了苏联翻译界的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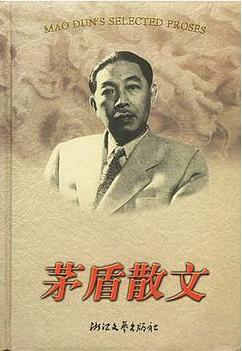
— —
影响翻译文本“进口”与“出口”的因素
中华民族具有广博的胸襟与气度。异国文化艺术融入本土传统,是一个鉴别、选择、消化、吸收与扬弃的漫长过程。
而影响文本“进口”与“出口”的因素,首推社会意识形态因素。这与一定时期国家政策和舆论导向有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钱钟书提到的清政府和刚才说到的苏联。
清政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公式,使其对他国文化文学的引进上带有明显的个体偏好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中国对外国文化的全面吸收借鉴,因此,直到后来由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人物的极力鼓吹和倡导,翻译文学作品才日渐纷繁芜杂起来,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而苏联呢,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品,都脱不了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性的谋求。因此外国人必读意大利文学名著,国家政策与舆论导向对于文化的“吸渐”意义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极其注重对文化媒体的监督和管理。

本站声明 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学习参考。

李欧梵人文六讲:文学与电影的关系,经典的